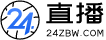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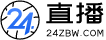

导语:
时隔半个月,在塔利班宣布战争结束的第二天,25岁的阿富汗短跑选手尤索菲·基米娅更新了她的INS。那是一张她跟跆拳道选手曼苏里·法扎德共举阿富汗国旗准备进入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现场的照片。这回她的波斯语配文有些悲怆:
“我亲爱的祖国,他们是何等残忍使你孤身一人,他们是何等残忍蚕食你宝贵的领土,两面三刀的敌人啊。不知这是否是我最后一次把荣耀的国旗带进赛场,不知我是否还能再戴着写着你名字的荣耀头带比赛,我只知道这不是我们的权利。我亲爱的人民,亲爱的女孩们,愿真主保佑你们。”
凤凰网体育《凰家看台》出品
文|凤凰网体育资深作者丰臻

基米娅本可以骄傲地离开东京,回到祖国享受荣光。
就在塔利班对阿富汗政府控制的大城市发起全面进攻的7月30日的下午,她正好在参加女子100米预赛。并不意外,她只拿到了小组第7,没有晋级下一轮复赛。她有些失望,一如摄影师在她冲过终点之后拍到的懊恼的表情。那天她说:“我为了更好的结果来到了远方,结果却没有用。”不过,她还是足够优秀了。
过去几年来,基米娅一直是阿富汗跑得最快的姑娘。这是她第二次参加奥运会,跑出了13秒29,比5年前在里约的14秒02提升了0.73秒,刷新了自己创造的阿富汗女子百米全国纪录,这总归是件开心的事。但阿富汗人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即便是她自己,也在完赛之后把奥林匹克抛到了脑后。她每天上推特刷阿富汗内战的最新消息,她给政府安全部队点赞,跟一个支持塔利班的巴基斯坦女演员反复打嘴仗,她痛批一些政府首脑是只懂权力和腐败的行尸走肉,跟塔利班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基米娅还能憧憬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那时候疫情应该结束了。几天前她还很有信心地转发过总统高级顾问莫尔塔扎维说的一席话:“塔利班就像一个日冕,这一波很快就会消失。”但现在她知道那是政客在做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宣传。
对基米娅而言,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充满了可怕的未知数。
基米娅应该庆幸还是悲哀于自己父母成了被迫离开坎大哈的难民?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她在阿富汗长大,她难成这么优秀的运动员。
1995年,塔利班正式掌权,阿富汗女孩子不被允许参加工作甚至不能独自出门,更谈不上进行体育活动。混乱局势下,基米娅一家成为了流落到伊朗的80万阿富汗难民的一部分。1996年,基米娅出生在伊朗城市马什哈德。

困在他乡谈不上多好,但伊朗的生活给她带来了很多。她的几个兄弟都很热爱运动,所以鼓励她尝试成为一名跑步选手。成长的过程中,基米娅把伊朗女子短跑运动员玛丽亚姆·图西视为偶像。
那也是一个戴头巾穿长裤比赛的伊朗姑娘,创造过女子100米、200米和400米的国内纪录,也曾是400米的亚洲冠军。图西很飒,INS上尽是她戴着各类帽子和头巾的美照,她是很多穆斯林女运动员的榜样。
2013年,基米娅17岁的时候,本·拉登已经死了5年,塔利班政权被美军的炮火赶进深山很久了,需要女运动员的阿富汗新政府发现了她并把她带回了祖国。在喀布尔的简陋的体育场里,可以随意进出的人习惯一边坐在场边闲聊,一边看一个穿黑衣黑裤戴着黑头巾的姑娘在跑道上训练。对阿富汗女孩而言,哪怕周围的模样有些异样,这也已经是一种幸福。
基米娅幸运在,以运动员的身份享受到了在奥运会上代表祖国的乐趣。开幕式上,作为旗手的她穿着阿富汗传统服饰,以微笑告诉世人,阿富汗就是阿富汗,没有因为不停的战争而粉碎。

这或许就是奥运会的意义。但另一面,可不是这样的。5人代表团背后的凄凉,无论如何是藏不住的——那一刻全世界只有阿富汗在打仗。奥运会和体育是他们的临时避难所,是乌托邦,但她们还是要回到现实中。
从避免战争伤亡的角度来看,所幸,这场战争结束得很快。8月15日,塔利班顺利攻占了首都喀布尔,表示阿富汗战争已经结束,将协商建立开放包容的伊斯兰政府,并采取负责任行动,确保阿富汗公民的安全。有消息称,塔利班还颁布了一系列新政策:组建多党派联合政府、死刑由法院而不是宗教法庭裁决、允许媒体批评政府、允许妇女单独外出,工作和接受教育等等。显然基米娅还不敢相信这些承诺。
就过往体验而言,满目苍夷的阿富汗曾是体育世界里的一个黑洞。
历史上最惨淡的一次奥运会就跟阿富汗有关。1980年苏联举办的莫斯科奥运会遭到50多个国家的联合抵制,抵制的国家里既有冷战对立面的美国、日本,也有正在打开国门要跟西方搞好关系的中国。英法等国虽然参加了,但没有以国家名义参赛,是以奥林匹克会员身份参赛。中央列宁体育场的氛围极其尴尬。这些国家联合抵制莫斯科的原因在于:前苏联在1979年年底入侵阿富汗。

最终只有70多个国家参加莫斯科奥运会,门庭最冷落的一次。面上是奥运会所推崇的和平的宗旨,背后是国际政治、军事在中亚的角力。刚刚开始没几个月的苏阿战争,提前给莫斯科奥运会拉上了幕布。有意思的是,阿富汗以国家名义参加了这届奥运会。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爱尔兰人基拉宁曾这样描述:“这场奥运会掺杂了太多不属于运动的因素,团结、友谊等因素全部荡然无存,只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仇视与敌对。”
你很难说阿富汗是在这场奥运会漩涡之中,还是旋涡之外。但战争对百年奥运会而言只是插曲,对阿富汗却是沉重的宿命。
苏阿战争打了10年,打到苏联快要解体,打到阿富汗千疮百孔。阿富汗人没过几年安稳日子,塔利班在1995年上台了,这是一次让阿富汗更加远离主流世界的政权交替,至少体育如此。阿富汗被国际奥委会取消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及其它所有洲际赛事的参赛资格,他们的理由是:塔利班禁止阿富汗妇女接受教育、参加体育运动,他们甚至把喀布尔的哈兹体育场作为公开处决的刑场。
状况持续到塔利班政权第一次被推翻才结束。2002年,阿富汗体育重新进入国际奥委会版图。2003年巴黎田径赛世锦赛,一座现代体育场馆都没有的阿富汗,终于第一次有女运动员出现在世界大赛上,这名短跑选手的名字叫利玛·阿兹米。
儿时的阿兹米几乎没有进行过体育训练,她只能待在屋里读一些简单的书。塔利班倒台后她得到了读大学的机会,那年正在读大二的她,因为被发现比其她女孩子跑得快一点,于是被挑选去参加巴黎田径世锦赛。世锦赛开赛前3个月她才开始进行短跑训练。到巴黎前,她只两次尝试过在有起跑器的情况下练习起跑。
阿兹米得到的这个参赛的资格,有外卡性质,是来自国际田联的特殊关怀。体育有时候总能以得体的方式承担“团结”的作用。
巴黎法兰西大球场,阿兹米在阿富汗女性参加的第一场世界大赛里,第一次在室外公共场合露出了她的手臂和头发,她花了漫长如半个世纪的18.37秒跑过了100米。无论如何,她到场了。

女运动员的处境不会顷刻变好,她们从整个族群保守的意识形态泥潭里挣脱出来的过程充满艰辛。正如参加雅典奥运会的阿富汗柔道女选手法丽巴·礼萨伊所言:“僵化的父权统治性别角色”仍给她带来很大束缚。后来,19岁的阿富汗田径运动员马赫布芭·阿哈德贾尔在一次海外训练营中收到了极端分子的死亡威胁,她被迫草草结束她的训练,这是最真实的例子。
但阿富汗的女孩还是前赴后继了。百米赛道上,阿兹米之后,是罗比娜·穆基亚尔。
阿兹米在2003年巴黎世锦赛上顺利完赛,帮助阿富汗获得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百米的参赛名额,拿到交接棒的是罗比娜·穆基亚尔。17岁的穆基亚尔跟阿兹米有相似的童年经历,但她在体育老师苏拉特加的带领下,备战工作更专业了。苏拉特曾因为是女性被塔利班政府剥夺了工作,错过了太多,她把梦想放在了穆基亚尔身上。
穆基亚尔在雅典跑出了14.06秒,比一年前的阿兹米快了4秒以上。而且这回她真正取得了胜利——她排名倒数第二,至少为阿富汗战胜了一位选手。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罗比娜·穆基亚尔再度参赛,这回她跑出了14秒80,没能突破自我,但这次事出有因。原本要来北京的是另一位选手阿哈德娅,但阿哈德娅收到了阿富汗极端分子的死亡威胁,放弃了参赛资格,跑到挪威去避难。银行上班的穆基亚尔在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剩2周的时候,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训练。
穆基亚尔没能刷新自己的百米纪录,但她收获了鸟巢观众集体送给戴头巾穿长裤跑步的选手的掌声。穆基亚尔说过:“阿富汗女性能来参赛,本身就相当于一枚金牌。”
一旦开始了,阿富汗在女子百米上的传承就不曾中断。2012年的伦敦,塔米娜·科西斯塔尼接过了穆基亚尔的交接棒,成为第三位站在世界大赛百米跑道上的阿富汗姑娘。塔米娜说,正是穆基亚尔在2004年雅典的表现激励了她走上了跑道。塔米娜在伦敦碗跑出了14秒42,虽然没能刷新穆基亚尔在雅典创造的纪录,但刷新了她自己的最好成绩,也不失为是一种突破。
塔米娜比前辈更近一步在于,她公开表态会在阿富汗运作一个叫“阿富汗妇女运动”的计划,希望帮助更多女性通过体育运动来进一步争取自己的权益。“我来自一个每天都有自杀炸弹袭击的国家,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女人处境艰难。许多人希望阻止我训练、参赛,但我还是来了,这对我和我的国家都意味着很多,我能参加奥运会就是一个奇迹。因为社会和家庭的问题,许多阿富汗女孩不能从事体育运动,我要告诉她们:和我一起来吧!”
尽管后来这个计划因为重重阻力而搁浅,但群体意识上的转变在悄然发生。从阿兹米的18秒37到尤索菲·基米娅的13秒29,这一路没有白跑。

就跟摇滚乐在喀布尔越来越受年轻姑娘喜欢一样,阿富汗的女性体育运动这些年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早在2006年,法国“运动无国界”组织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筹办了首届女子运动会项目包括篮球、空手道、柔道、排球和跆拳道。那是一次公开的尝试,试图消解传统禁忌,政府持鼓励态度。时至今日,喀布尔的健身俱乐部已经不少了。据西方媒体报道,女子拳击在那里颇受欢迎。还有人发现,中国的武术俱乐部都开到了喀布尔,收了不少女子学员。
现在局势下,基米娅是悲观的。这种悲观不只来自于她对塔利班的认识,还来自于现实的迷茫以及无所依靠。她在推特上最新关注的一条内容,是一位女记者的发言:“这片土地上的穷人今天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是由于多年来欺骗人民并充实他们要报的领导人和政客的无能导致的。”
这句愤慨的抱怨下面,基米娅留了一个简单的评论:“对。”
她还能戴上她那条额头上印着Afghanistan字样的黑色头巾跑到巴黎去?还有没有另一个姑娘冲破阻碍接过她的棒?答案在喀布尔混乱的街头飘扬。
